晓晨
昨天,老家的人来省城,捎来了一箱家乡产的小米。早晨拆开包装,一股清新米香扑面而来。黄澄澄的米粒,饱满圆润,抓一把在手里,扑簌簌如沙般从指间泻下。煮了一些下锅,不一会儿,满屋便飘满了诱人的香气,并钻出门缝,索绕在走廊里。我想,邻居们也许都在忌妒是谁家的美味吧?
这香气,马上勾起了我一些关于小米的难忘记忆。老家所在的位置,在黑龙江与内蒙古交界处、松嫩平原的边缘,耕地主要以漫坡岗地为主,沙石土质,很适合谷子生长。因此,虽然这种作物产量很低,但家家户户都种植,是当地主要的作物品种之一。每年开春,积雪消融,犁过的土地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,村民将谷种均匀地撒在剖开的一条条垄沟里,再用一种农具将垄沟合拢上。这样,几场春雨,垄上就冒出了一趟趟新苗。远望去,整片谷地就如一块巨大的绿色的条绒布。这时,总有布谷鸟不知在什么地方不停鸣叫:布谷布谷声音时远时近。记得,幼小的我当时总为一个问题大伤脑筋:布谷鸟是怎么知道大家都在种谷子的,它怎么从不关心苞米和高粱呢?
想着想着,就走了神,直到头上“啪”地挨了一巴掌:“发什么呆,又把谷苗儿拔掉啦!”爸爸的斥责,将我从漫无边际的冥想中扯回来。
家里能干活儿的人手不多,放学后我常被大人抓来到地里拔杂草。但我实在分不清,哪些是稗草,哪些是应留下的谷苗,因此常免不了皮肉之苦。而且拔杂草这活儿,也真的很累人,开始还好些,弯着腰,但时间长了,就成了蹲坐在地上一步步向前挪。半天下来,就累得腰酸腿软,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长垄长吁短叹,双手也被草汁染成了墨绿色。好不容易挪到了地头,又要折回来开始下一垄。因此,小时候梦中经常出现两个痛苦的场景:一幕是在课堂上面对天书般的考卷;另一幕,就是蹲在田野里望着前面没有尽头的地垄沟。
春天的云,白得跟棉花糖似的,一朵朵在天上跑得飞快,一边不断变幻着形状,匆匆如赶集似的奔天边去了。有时偷个懒儿,躺在垄沟间伸展酸麻的腰肌,简直舒服极了。闭上眼睛,对着暖洋洋的午后的太阳,眼前红通通的一片,能看到眼帘上细红的游丝在滑动……又开始神思飞扬起来。
来源:黑龙江日报
以上是网络信息转载,信息真实性自行斟酌。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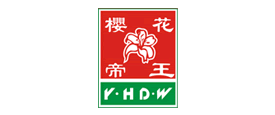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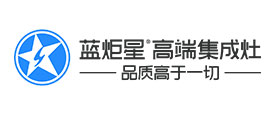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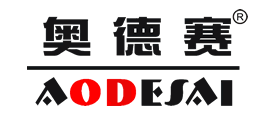





 )
)









